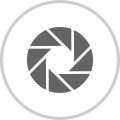照片上的陈东东,大多是黑白照,且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张——像是动画片Snoopy里的老实人查理。大鼻头,眼镜背后藏着两颗黑豆,一点无辜,一点忧愁,仿佛对着掌镜的人无声地发出“嗯?”的轻问;两小簇眉毛毫无攻击性,也没什么存在感。
 【资料图】
【资料图】
朋友们一旦过了60岁,他便在文章里给他们加个前缀——老北岛、老多多。如今他也到了这个年纪,紫色诗集摆在一旁,作为他过往40年成果的浓缩证物。多多曾说,“诗人/的原义是:保持/整理老虎背上斑纹的/疯狂”。
以此为标准的话,陈东东似乎不太符合。他曾引用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提到的“火焰派”(随时间而成长、消耗其周围物质的写作风格或方式)和“晶体派”(结实、理智、透彻、潜在、内敛、明晰、冷笑话的),坚称自己属于后者。
这种风格外化于旁人的评价,美化的是,“似乎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某种安静、冥想的气息”;直言不讳的,则是“很少说话、相当内向、不容易接近”。他深表认同,总是迫不及待地向来访者提前声明,自己面对陌生人的羞涩和不知所措,不会喝酒,不会抽烟,讷于谈吐,不懂交际,以及,口才不好。这样对方在听到类似“基本上只有在要写这首诗的时候你才会去写这首诗”的含混表达时也就不至于太惊讶。
比起一对一的采访,他更害怕朝向公众的发言和表演。1984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所高中做教师,强撑了两年,便“主动、坚决地离开了讲台”。他是学校里极少数不用做班主任的语文老师,逃避了召开家长会时置身一屋子陌生人中间的麻烦与慌乱;也是为数不多从不给学生打不及格、放学后还会应邀跟他们一起打牌的老师,多次被教导主任叫去办公室训话。
同事们对他的做法充满疑惑,而他对旁人司空见惯的举动也同样深感不解。他们习以为常地利用课间时间在办公室里要么闲适地择菜聊天、要么板起脸给不听话的学生点颜色看看。现在回忆起来,陈东东的口吻里仍透着不安和惶恐,仿佛彼时承受了那些屈辱和谩骂的,并不是某个倒霉学生,而是角落里默不作声的年轻的他本人。“我上课也有调皮捣蛋的,但我从来骂不出口,很难听的。”
受益于十分宽松的成长环境,父母对他几乎从无管束。没有检查过一次作业、问过一次分数。唯独在高考填志愿时,母亲做了干涉,将他写好的外地院校划去。自此,那些报考地质或航海专业、加入探险队,去漂流或寻找巨人、野人和雪人,成为职业旅行者,退而求其次导游也行的美好愿望,都成了空想。
留在出生地的陈东东,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在那里遇见了室友王寅。“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诗人了。我刚开始写诗时受到的影响都来自他,来自他抄录在一个——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的——红色塑料封皮的笔记本里的聂鲁达、泰戈尔、艾青、维尔哈伦、蒙塔莱、庞德、阿莱桑德雷和艾吕雅。”他几乎照单全抄了那本笔记本里的翻译诗,也从那里第一次接触国内诗人,读到了北岛、江河、舒婷和顾城。
他和王寅等人创办了名为《倾向(WM)》的诗刊,在大学期间便开始认真地、狂热地写诗,并意识到“诗是一生的事情”。教书之后,他发现这项事业和写诗一样,都需要全力以赴,权衡之下,只好放弃前者。“在写作的技艺方面,我那时似乎初窥门径了。我写得相当多,很难去顾及其他事情,热情如高烧不退。”
“那幢大楼不断出现在我的写作里”1986年,陈东东离开任教的学校,到位于外滩的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上班。几年前他再次前往香港路,发现曾无数次进出的地方如今已成了危房。他在门口徘徊一阵,拍了一张照后便黯然离开。
他上班后不久,诗人钟鸣来上海,被带进那幢大楼。那幢位于黄浦江、苏州河之间三角地带的、有着科林斯式列柱柱廊的古典复兴风格的大楼。目睹陈东东像卡夫卡一样呆在阴暗的办公室里,“如果有什么使别人坐立不安,那肯定是他的枯坐。”
在当事人看来,事情倒并非绝望到一无是处。他供职于“史料室”部门,名义上要做的事情是整理旧工商史料——摘抄《申报》,帮那些原工商业者、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修订甚至代写回忆录,后来又参予上海地方志的撰写。
置身清闲的办公室,也许,一个月的公事可以在三小时内就办完。剩余的时间他便用来写诗、读书,甚至溜上大街,到外滩散步或跟朋友喝茶。上司和同事们认定这是个没什么抱负和出息的人。“爱向上爬的同事较喜欢我,因为我对他们毫无威胁。谁也不知道我那么认真专注地伏案在办的那件公事,竟然是一首诗。”
“广场的大理石覆盖着地下金库,那里面贮满了金条、银元、英镑和鸦片。”他曾集中地写过那幢大楼,取名《回字楼》。“实际上,那幢大楼和它(风格)的变体不断出现在我的写作里。它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历史的和象征的。它成了我的写作也许不浮出水面的一部分,尤其当我做出决定,再也不走进那幢大楼以后——它名符其实地成了我在写作中即使忘却也一样存在着的一部分过去,一种氛围。”
坐班十几年后,他于1998年辞职,在21世纪所有突变来临前过起安静本分的生活,专心投入写作。他喜爱一个叫康拉德的作家,眼热其漂泊二十多年、行万里、真正称得上“浪迹天涯”的诗人生涯。
回望自己的前半生,发现它单调得一目了然。“只是从家里出发去学校,尔后则改为每天去一幢毗邻黄浦江的大楼上班,坐在一间档案史料室里凭窗翻看旧《申报》缩印本。这种日子,我过了很多年。”
于是他自然又想到博尔赫斯,这位20岁出头就扎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著名作家,成了他的榜样和对未能如康拉德般周游世界的自我慰藉。
而作为中西文明交汇之地的上海,也给了诗人漫长的滋养。在起步初期,他便见识了上海的眼界,“在我这儿,有时候甚至是让我略感不安的冷淡。譬如1983年顾城来我们学校演讲,我并没有去听,只是中途路过,在后排看了一眼就离开了。”
“上海的好天气集中在秋天,特别是上午,安静、明澈,这既是状态又是氛围,笔尖在白纸上可以像航空公司的喷气式飞机在晴空里划一条漫长的弧线。”这里是他创作的稳固场所,更为他与好友的交往任劳任怨地提供着适宜的布景。
其中一位是“上海女婿”张枣,自从1996年将近春节时回上海后,他就一次次频繁地到上海。陈东东记得,张枣最爱上海商城一带的南京路街景,笑盈盈地赞叹:“我回长沙,每天要经过的一个高架路的拐弯,竟然是锐角度的,司机每次开过都要骂娘……可是上海真的做得好,很现代……”
1980年,上海,与大学同寝室同学王寅等在上海师范学院合影(受访者提供/图)
他与张枣玩心理测试游戏,要他依次说出自己最喜欢的三种动物,然后告诉他,他第一喜欢的动物代表自以为的形象,第二喜欢的代表别人眼中他的形象,第三种则是他本人真实的形象;跟他从吴江路上红烧狮子头出名的“东方快车”小餐馆吃晚饭出来,重新走到南京路上,身陷于四周灯火通明的峡谷,张枣不免沉吟起来:上海,这座大都市里一定会有一个真正的去处,一个真正接纳诗人的去处……可是这个去处又在哪里呢?
看腻了海鸥,发现军舰鸟他将这些记忆的完整片段写进《我们时代的诗人》,文章皆从个人视角出发,“写的都是当代一些比较重要的诗人的故事,尽量不去做评论家或是教授课堂上讲解那样的写作”。书中选取了四位诗人,昌耀、食指(郭路生)、骆一禾、张枣,“其中三位诗人都已经去世了,我现在还在接着写一些诗人”,这个系列的名单最后包含二十多位。
他是极其推崇慢功出细活的人,从没想过那么快就将四篇专栏文章集结成书出版,由于本就写得匆忙,后续又做了很多补充和修改,但耐不住编辑一直追到飞机场要跟他签约,实在不好意思当面拒绝,只好同意先仓促地出一本,并反复交代,等二十多位全部写好了以后再出下一本。
“真正让作者本人放心的诗集近乎不存在,放心的程度总是与诗集的厚度成反比。”陈东东一度秉持这样的观点,最近诗集《略多于悲哀》印刷出来,他倒是松了口气,对整体颇为满意。一方面也许是他将之视为60岁的礼物,另一方面是新书展示了2016-2021年的最新创作,例如地方诗系列。
陈东东和张枣,2005,苏州(受访者提供/图)
早些年他曾坚定地表示,“相较于80年代那种明净、细致、口味挑剔的写作,我90年代直到近期的写作就相对开阔,相对和多少有点儿晦暗和不洁。”待到诗歌的创作年限拉长至40年,许多答案又模糊起来。如今他说,“我的变化就不像有些诗人那种阶段性明显的突变,而是像博尔赫斯的小说《皇宫的寓言》里描述的那样,宫里每隔50米就有一个塔。第一个塔是米黄色的,最后一个塔是深红色的,每个塔之间,颜色在一点点地变。阅历、阅读、写作的积累不一样,写到后面,就会有变化。但你非要我说出我的整个变化,自己很难谈明白。”
翻看几十年前写的那些诗,他恍惚觉得它们“像别人写的一样”。“那个时候写得挺好,刚写完,怎么看你都觉得还要改。但是很多年以后你再看这首诗,就发现它已经高度成型了,不能再去改动它。而且你现在觉得写的时候碰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音节上的处理,以前不是解决得挺好嘛。”
旁人评价他的诗,提到最多的一个是其诗歌结构中的音乐性,或许来自父亲是音乐学院教师、母亲是越剧演员的音乐家庭的耳濡目染,另外便是其语言的“唯美”。
印象派画家德加也写诗,有一次他问马拉美:“我弄不懂,这首小诗,我怎么就写不成,其实我脑袋里装满了思想。”马拉美回答:“德加,写诗靠的是词,而不是思想啊。”
陈东东诗里的词很早就展露了异样的光芒,在他们刚开始写作的1980年代,“语言很糟糕,有很多陈词滥调。”看腻了“野鸽子”“海鸥”,他刻意在动物园找一些奇怪的鸟;加上中学时反复翻读、临摹的插图版《希腊神话与传说》,所用意象往往叫人眼前一亮。
《文学报》上的评论文章是这么评价陈东东的作品的——
“他的诗歌基本上都是及物的,但又不是写实主义,意象非常丰富,与他的视野开阔和阅读有关。他的意象中既有自我经验、中国经验,又有间接的来自书本的西方经验,特别是这种海洋性的意象,比如军舰鸟、鸥鸟、海神,我们农耕民族就觉得非常奇异。他诗歌中的海洋气息和埃利蒂斯的海洋文化有一种互文关系,希腊的阳光明媚,对于人的赞美这种精神和我们东方人对真善美的爱,也有契合之处。
“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写上海生活的文本,有一句写的是从桥上下来的双层大巴士’在银行大厦的玻璃光芒里缓缓刹住车’,太棒了。这首诗的名字叫《外滩》,没有在上海生活过,或没有感触的写不出这样形神兼备的城市经验。”
关键词:
相关内容
- 环球今热点:陈东东:谁也不知道我伏案在办的公事竟然是一首诗
- 全球速读:今年经满洲里站进出口运量同比增长42.4%
- 魏微《烟霞里》:一场艰难而快乐的跋涉
- 世界简讯:第33个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举行 内蒙古全力保护1.72亿亩耕地
- 轮椅女孩赵红程的“无障碍”话剧:我让你感到紧张吗? 天天热消息
- 中国恒大中心更名万通保险中心,云锋金融:为主要租户,从未购入任何业权 世界热讯
-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京津冀地区招商推介成果丰硕
- 全球今日讯!锐捷网络(301165):6月26日北向资金增持61.24万股
- 好评众多!王宝强电影《八角笼中》将上映:他说要把金扫帚奖还回去 天天快资讯
- 天天头条:快看!河南省近三年本科二批平行投档分数线来了!
- 世界新消息丨肉鸡腺胃炎应提前预防
- 黄金收盘:美元汇率走软 黄金及白银期货收盘走高|当前热议
- 【速看料】21克拉钻石多少钱一枚_21克拉钻石多少钱
- iPhone 15量产在即:先备货8500万台 头条
- 工信部副部长会见联发科技董事长蔡明介
- 2023世界半导体大会7月在南京举办_焦点资讯
- 每日速讯:5月末中国农行制造业贷款余额突破2.8万亿元
- 天音控股;中原信托相关事件对公司长期经营无影响
- 泛海控股董事会选举栾先舟为董事长
- 氧化铝期货为产业发展提供新工具 当前速讯